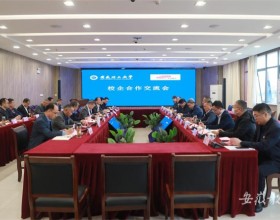12月4日,有媒体曝光:云南先锋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锋公司”)污染问题突出,曾被停产整治后又擅自复产。针对此事,云南省环保厅通报称,12月5日,该厅组织省、市、县三级环保部门进驻先锋公司,就企业存在的环境违法问题约谈了企业负责人,下达了《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要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立即组织落实停产决定,进一步加强整治,消除对周边环境和民众的影响。
通报还称,先锋公司褐煤洁净化利用试验示范工程自2014年投入试生产以来,由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恶臭异味污染影响一直受到民众投诉。省、市、县环保部门按相关法律法规对先锋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多次责令整改并作了处罚。2016年5月,云南省环境保护厅责令先锋化工停产整治。先锋公司对存在的环保突出问题进行了整治,2016年11月1日起擅自复产,但由于各种原因,尚未从根本上解决恶臭异味影响的问题。云南省环境监察总队于2016年11月22日对该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并明确提出了停产要求。
云南省环保厅表示,下一步,该厅还将分设现场执法组、资料调阅组、外围环境检查组、监测组、社会维稳组五个小组开展调查工作。省、市、县各级环保部门将严厉查处企业的违法行为,监督企业停产整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整改落实。
延伸阅读:
云南先锋化工有限公司环保相关情况通报
12月4日晚,央视《经济半小时》对云南先锋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锋公司”)污染情况进行了报道,对此,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要求立即组织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12月5日,省环境保护厅组织省、市、县三级环保部门进驻先锋公司,就企业存在的环境违法问题约谈了企业负责人,下达了《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要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立即组织落实停产决定,进一步加强整治,消除对周边环境和人民群众的影响。下一步,省环保厅将分设现场执法组、资料调阅组、外围环境检查组、监测组、社会维稳组五个小组开展调查工作。
先锋公司褐煤洁净化利用试验示范工程自2014年投入试生产以来,由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恶臭异味污染影响一直受到群众投诉。省、市、县环保部门按相关法律法规对先锋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多次责令整改并作了处罚,2016年5月,省环境保护厅责令先锋化工停产整治。
先锋公司对存在的环保突出问题进行了整治,2016年11月1日起擅自复产,但由于各种原因,尚未从根本上解决恶臭异味影响的问题。省环境监察总队于2016年11月22日对该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并明确提出了停产要求。
下一步,省、市、县各级环保部门将严厉查处企业的违法行为,监督企业停产整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整改落实。
云南省环境保护厅
2016年12月5日
还有多少享受“特殊待遇”的污染大户
7月15日,中央环保督察组开始了云南省的环保督察工作。仅仅半个月时间,中央环保督察组就接到群众对一家叫做云南先锋化工的企业高达46次的投诉和举报。11月23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云南省委、省政府反馈了督察情况。又一次点了这家企业的大名,督查组指出:“个别企业环境问题群众反映强烈,云南先锋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的恶臭污染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面对持续性违规排污,云南先锋化工公司却表示,即便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也无所谓,因为他们的企业很特殊。
面对地方民众的常年投诉与中央环保督察组的专项整治,这家企业却依然能够坦率说出,“即便违规也无所谓,因为他们企业很特殊”,显然突破了人们对于一家违规排污企业应有形象的设定。所谓“特殊”的原因并不复杂,无非是因为其属于当地重点企业,是地方政府区域经济的台柱子、财政的钱袋子,从而在环境治理中,获得了某种近乎公开化的区别对待。
从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不能说当地环保部门对于这家“特殊”企业的任性排污完全无动于衷。仅2016年,云南省环保厅就多次对该企业采取了行政处罚与停产整顿。但问题也正在于此,这边是看似严厉的违规处罚,那边企业却依然我行我素——相关部门完成了“治理任务”,企业的违规生产也不受影响,由此,在环保部门与企业之间达成了某种隐性的平衡。只不过,维持这种畸形平衡的,并非只是环保部门的不作为,而是更源自某种超然于环保治理之上的地方袒护。
当地政府维持这种“平衡”的努力,处处可见。2015年6月,在云南省环保厅对先锋化工等各种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后的不到一个月,该企业就成为当地一场生产活动会议上的座上宾;2016年4月,云南省环保厅又一次对先锋化工的违法行为做出处罚,然而仅在两个月后,昆明市领导就前往先锋化工参观,并表示要“重点扶持一批财政绩效大的企业,培植税源,支持经济良性发展。”此外,在企业选址时,先锋化工的特殊地位就已经展现。作为煤化工项目,本应远离居住区,但先锋化工五公里范围内却有大量的村落和居住区。可见,先锋化工自称的“特殊”并非虚言,而是体现在当地政府方方面面的照拂与区别对待之中。也正因为此,其获得了某种“屹立不倒”的特权。
是污染大户,但更是税收大户——当地政府显然是以实际行动对先锋化工作出了这样的排位。而地方政府所展现出的这种价值序列,与企业不惮于说出的“我们很特殊”,不过道出的是当前某种有着普遍性的污染治理真相:一方面,在不少地方,仍有地方政府将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而为了确保一时的经济指标,污染大户依然可以享有违规排放的“豁免权”;另一方面,较之于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违规偷排,地方政府囿于财政收益而主动对污染企业放行和袒护,其恶劣影响与负面示范,显然危害更甚,这恐怕也是当前环境治理最应该攻克的“堡垒”。
最严环境治理时代,特权污染户的存在,无疑是一种反讽。它不仅影响着环境治理的整体进度,也吞噬着人们对于环境质量改善的信心。究其原因,既与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之处理的失败有关,更或源自不少地方对粗放式发展模式的依赖仍在延续。就此而言,拥有特权的污染大户的存在,不仅仅是一种环境治理的危机,而更是一种发展的危机。而个案的纠偏之外,还有多少享受“特殊待遇”的污染大户在任性排污,如何突破传统发展模式对于环境治理效力的消解,显然值得更多的地方反思与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