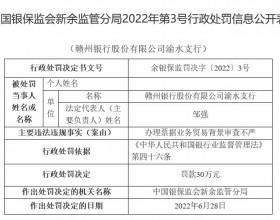这可能是史上最昂贵的一张纸条了。成人手掌大小,边缘破旧卷起,一面已经用过,另一面手写:
“今收到张秋莲交来煤矿入股款人民币贰亿贰仟万圆整。”
落款签字龙飞凤舞:刘旭明。
2013年3月13日下午3点多,同样的签名留在一张拘留证上。警察要求刘旭明用正楷一笔一画重写,按下手指印。接着,这位1983年出生的年轻人被送进陕西神木县看守所,留下“陕西历史上最大的集资诈骗案”于身后。
曾经,在神木“刘旭明”三个字只要落在类似股权收据类的纸上,就意味着结算时数倍于投资的回报。没有人在意合同、股权书的体面与正式与否。无数个刘旭明和“张秋莲”们织就了一张中国煤炭富翁的脸谱图。他们与中国能源经济一起崛起,一起癫狂。现在,随着刘旭明被抓,他们也一起面临大崩塌。
7月15日,数千民众在神木县政府门口聚集,与赶来的武警形成对峙之势。起因“县领导要跑路”谣言引起的群体事件通过网络传遍全国。这个往日盛产煤老板的地方到底怎么了?
《财经天下》周刊记者在7月23日来到陕西省神木县。在这座不到50万人口的小城里,类似于铂金汉宫国际大酒店这样名字和装潢看上去同样气派的酒店,比比皆是。只不过,在昔日最热闹的地方之一--麟州路和神华路十字路口,过街天桥上空空荡荡,偶尔只一两个孩子上去看看街景。随便找街边的人问,他会向你描述,这里之前随处可见路虎、保时捷、宝马,劳斯莱斯、宾利等也不是稀奇货。
末了,他会加上一句:“现在神木不行了,车少了一大半。”
相较而言,十字路口往北不远的神木县法院附近人流大些。人们大都神情麻木、眼神木然,从法院门口进进出出。上前去问,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为打官司要债而来。“这里前段热闹得像是菜市场。”有人描述说。
从2004年开始,神木人卖煤而富。当地政府于2008年开始推行城乡15年免费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实现“零收费”;2009年3月,实施全民免费医疗,成为全国第一个公费医疗“特区”。神木人介绍自己的家乡时,会说这里是杨家将的故乡,但外省人的印象中,神木更像是“中国的科威特”。
这一切都源于老天给神木的财富:煤炭。根据神木县政府的公开资料,全县59%的面积下都有煤,总储量达500多亿吨。而且都是世界少有的优质动力环保煤和气化用煤。近10年来,神木人大发煤炭财。一年有上亿吨煤炭是一大批暴富的煤老板。据《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统计,高峰时期神木县资产过亿元富豪人数达2000人之多。
当时,随着煤炭价格的高企,煤老板们开始掀起“炒煤矿”风潮,高息民间借贷随之蔓延整个神木。开始时,借贷关系大多发生于朋友、熟人间,但后来人们胆子越来越大,把巨款借给八杆子打不着的人已经很常见了,有时候甚至还要托关系才能把钱借出去,目的就是想借煤炭价格高企的东风,分一杯羹。
谁也想不到,在连涨了近10年之后,自2012年开始,煤炭行情迎来了拐点。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不少煤炭品种的价格都跌去了一半。进入2013年下半年,煤价还在继续下行。受此影响,神木上百处煤矿停工,一大批煤老板密集破产,民间借贷链条更是瞬间断裂。
对于那些靠高利贷去收购煤矿的煤老板来说,当煤矿急剧贬值后,很快便资不抵债,只好跑路。2012年底以来,神木失踪的老板多达200人,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4786起,涉诉金额初步估计超过百亿元,涉诉人数将近8000人。“前几年神木人见面,都问:你最近投了多少?现在见面都问:你要回来多少了?”一位当地人这样形容。
这其中,以“黄金大王”张孝昌和“集资大王”刘旭明最为典型。2011年5月始,刘旭明在神木放出消息,在内蒙古阿拉善盟获得一处约12平方公里的优质煤矿,希望大家出钱入股一起开采。事后证明,这成为刘旭明大规模集资的平台。
作为神木煤老板遭遇的一个典型案例,刘旭明从一无所有到意气风发、再到如今破产落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神木这座县城--也是整个中国煤炭富豪的真实写照。
神木往日风光已逝。随着民间借贷资本的破裂,房价暴跌、商业萧条、医保欠款、社会解构等难题,就如一张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将这座曾因煤炭资源而促使民营经济飞速发展的县城陷于苦苦挣扎之中。而在其依旧繁华奢靡的表面背后,是民间借贷崩盘引发的恐慌,以及泡沫经济破裂之后带给这座县城挥之不去的忧伤。
80后煤老板的崛起
在神木年轻人眼中,刘旭明是白手起家的梦想样板。1983年8月,刘出生于神木县最南端的万镇黄石畔村,家里日子过得并不富裕。2002年,刘考入西安科技大学读专科。据刘旭明一位校友称,上大学时,刘旭明开过小超市挣钱。这是他最初从事的商业活动。毕业后,刘旭明在一家内蒙古的洗煤厂上班,工作不到一年就辞职单干,开了个私人洗煤厂。这次冒险让刘旭明赚了一笔钱,他用赚来的钱买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车:别克。“在2006年,这是相当牛气的一件事。”贺峰说。贺峰比刘旭明小两岁,在内蒙乌海买有煤矿,与刘旭明同处一个煤老板圈子。
此时的神木,正处于煤炭经济的活跃发展期。从2001年开始,中国经济强大的需求推高了全世界的大宗商品价格,煤炭当然不例外。以6100大卡的电煤价格为例,2002年只有150元左右,而到了2010年,已经涨到了800元以上。
就在煤价大涨的同时,神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开始大跃进。包神、神朔、神延等运煤铁路相继开通,特别是2006年3月建成通车的神朔铁路复线,极大地增强了神木煤炭外运的能力。中国过去轰轰烈烈的投资建设使得能源需求井喷。大发其财的煤老板都牛气哄哄,付款时有的只认现金,连汇票都不想要。
刘旭明当时还没回到神木,在内蒙做政府做一些煤矿的投机生意。在此期间,他误信别人买了个无煤的矿,赔了一大笔钱,差点就此栽倒。贺峰说,此事之后,他开始明白,“挖煤其实风险很大”。
幸运的是,刘旭明买到了神华集团的一块边角煤区。挖了一阵赚到一笔钱后,他把煤田按块分开,转包给来内蒙淘金的煤老板,只留管理权在手中,一年稳当收取几百万管理费。“比如20万平方米的煤田,刘旭明自己挖可能赚100万,而划分成4份后,一份50万,直接就赚了200万。”
也正是从2006年开始,全国的房地产价格开始上涨。由房地产带动的几十个行业一片繁荣,钢铁、水泥、铝材、玻璃等等行业产能增加,对动力煤的需求一路攀升。反映在刘旭明的生意上,这一波大行情帮助他完成了由小煤矿主转型为地方“煤诸侯”。
通过细分煤田再出卖的手法,刘旭明最大限度地抓住了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后来他的操作,基本是对此类手法的复制。”贺峰说,2008年刘旭明并购了乌海常洪口中山煤矿,成立了集“原煤生产、洗煤、炼焦、化工”等为一体的中山矿业集团。这一年,刘旭明25岁,出门谈生意时常开一辆奔驰或两辆加长凯迪拉克。
刘旭明给人的印象是“有关系、能办成事”,为人豪爽,仗义疏财。经营煤矿买卖日久,经常有人从浙江、北京等地赶来找刘旭明帮忙,托他买矿、卖矿,刘旭明往往都能办成。
他自认在看懂人心方面技高一筹,以有钱大款的姿态出现,努力表现出自己有帮别人赚钱的能力。商人高某认识刘旭明时,开一辆几十万元的车。刘旭明对他说:“以你的身份,开这样的车能行吗?”几天后,刘旭明赠给高某一辆价值200多万元的路虎。高某的亲戚是当地另一个大老板,过几天高某就放心地给刘放贷了5000万元。
这样的手段,在刘旭明筹钱开矿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是神木县煤老板在筹资中惯用的手法,屡试不爽。
全民皆贷
如果只停留于煤矿的开采、买卖,刘旭明的生意将维持在实业状态。在煤矿买卖过程中,刘旭明有时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民营企业,到银行寻求贷款困难重重,刘转而回神木寻求富人集资,煤矿买卖完成之后,再把钱连本带利还回去。在一次次的低借高还的循环中,他的生意逐渐脱离实体。
2008年的一天,胡荣刚在神木县遇见了西装革履的刘旭明。“当时刘旭明开着豪车,好多老板请他吃饭,并带我一起去。”胡荣刚说,他和刘旭明是多年未见的同学,再次聚首时,发现对方已然发达了。
“我觉得他做得挺大的,于是就相信他,给他投了钱。”
那时,神木县内借贷风刚开始不久,大多发生于朋友、熟人间。借贷最早来自煤矿,有些煤矿主为买下一座矿,需要在十来天时间内凑齐上亿甚至10亿的资金到指定账户,等拿下煤矿之后,资金再迅速加息返回。当地银行系统根本无法满足此类需求。
不过,神木人正慢慢对此习以为常。“500万元借出,49天时间,煤矿分红可以达到490万元。”贺峰说,这类事情经常在身边发生。神木县最高分红纪录发生在永兴乡,有人入股1万,分红时达600万。本刊记者到永兴乡探访,发现村子里只剩下外地人和几个本地老人,暴富后的村民都搬到城里去了。
2008年到2009年,胡荣刚把大笔资金借给刘旭明,投入到乌海的中山煤矿以及一个当地的煤厂,都获得了可观的分红,这让他对刘旭明佩服不已。
刘旭明的堂侄刘羽(化名),与胡荣刚的经历基本相似。2011年4月,刘羽遇到一个几年未见的朋友,这位朋友称当初借给刘旭明200万元,分红时连本带利分到380万。身边的财富事件深深地刺激了刘羽,于是,他想抓住刘旭明这棵大树,快速实现财富梦想。
刘羽从银行贷了几十万,又以月息3分的高利贷凑了700万,会同当地人吴义平和李云军,三人凑了4000万,分两次给刘旭明的会计刘彩英打款,买下了刘旭明所属中山煤矿一个井田。这天,吴义平记得很清楚,正好是汶川大地震3周年。刘旭明答应他们,20天内就能开工。
可等了两个月,中山煤矿依然未能开工。三人无奈找到刘旭明,希望能有个解决办法。刘旭明出乎意料的爽快,按月息3.5分给4000万支付了利息。刘羽、吴义平和李云军,每人都赚了可观的利息差价。
4000万对于三个普通人而言不是小数目--那是在中国其他地方,在神木,你需要的只是胆量。
2004年之后,受煤炭经济带动,神木的县城版图扩大了3倍,新房子修到了西边的河堤和山上,榆林“南六县”、延长、关中和西安等地的人纷纷云集于神木。神木的酒店、宾馆、KTV、餐馆、洗头房、汽贸等不断有新店开业。由于县城夹在东西两座山当中,“鞭炮隔一会儿炸一阵,动静非常大”。
急剧膨胀的实业需求以及煤矿价格的节节攀升,导致神木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炒矿所需要的资金不是小数目,这使得煤老板成为对高利贷需求最强烈的人群。在政府控制下的金融系统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对资金渴求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开始井喷。
2008年,神木县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成立,而后各类贷款公司、典当行等钱庄应运而生。到2012年时,神木县有银行类金融机构达21家,是长江以北地区银行最多的县;还有小额贷款公司22家,数量为陕西各县之冠,注册资本总额近27亿元。这还不包括大量的民间地下金融公司。
当地的陕西神木农村商业银行(即陕西农村信用合作社),推行了一项颇为激进的政策:只要有可靠的人担保,一两百万元的贷款无需抵押,只需签个字即可。早期的个人老板投资商铺或饭店,至少有一半的钱来自农村商业银行。
此外,通过熟人,当地人可以以月息1分的低利率从银行贷出钱来,然后放到典当行或小额贷款公司去,直接可以加到月息2分,甚至更多。只要能贷到款,就可以吃差价。这种模式,神木超过一半的人参与过。在神木有一句话,叫全民皆贷。这样的借贷,在煤炭业方兴未艾的鄂尔多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神木县法院后来公布的信息看,2011年审理的679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95%以上月利息在3分左右,甚至有的在3分半以上,而放款利息则普遍超过3分,有的达到了3分,折合年利息为60%,已经逼近当时煤炭利润的上限。
农村商业银行的激进做法,帮助很多人实现了梦想。负面影响是,此种做法扰乱了神木农村金融市场,造成高利贷全民普及,谁不参与谁就傻瓜。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风潮让人们逐渐丧失了本应该有的风险意识。
“这种做法几乎就是不劳而获,纯粹是数字游戏。”贺峰说,有人甚至凭借这样的手段一年赚千万以上。高峰时期,神木的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达到1000多家,甚至注册一个商贸公司、烟酒行都可以借款放款。慢慢地,似乎所有的人都有钱,都在找项目。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刘旭明告诉刘羽、吴义平和李云军,如果本金不退,将会有一个大煤矿,很快就能分红,比例是50%,“照顾一下你们”。
当时,吴义平有把大部分资金撤出、留下几百万入股的念头。毕竟,吴义平投入的2600万,大部分是来自高利贷。但是刘羽动了心,他主动去做吴义平的工作,劝他继续留下本金一起入股,“再入股一次,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
吴义平最终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为求心安,吴义平找到刘旭明,让他开具了原始股入股凭据。事后,刘羽向《财经天下》周刊坦言:“拿了刘旭明分红的人,极少数见好就收的,大多数人选择连本带利继续投入。”
类似与刘旭明做生意只赚不赔的例子通过口碑相传,使他迅速成为神木炙手可热的人物。刘旭明轶事流转颇多,早期的一个例子是,在乌海时,刘旭明看着一个开洒水车的小伙子实在,就给那人开了高薪,果断挖到自己公司。后来那小伙子跟着刘旭明发了财,买了丰田车,在乌海也买了房。
更为人所看重的,是刘旭明与神木政商名人间的关系。他通过王凤华、王凤义兄弟,接触到神木当地知名企业家王凤君、刘银娥等人。王凤君于2003年开始做化工行业,是神木煤炭经济转型的代表人物。而刘银娥早年以开小卖部起家,事业横跨煤炭、化工以及农业,成为县、市和省三级人大代表。“刘旭明与他们都有资金、生意上的往来。”吴义平称。
生意上声名鹊起,刘旭明同时开始走政治路线。2009年,他创建神木中学旭明基金,第二年出资200万元将基金扩充,先后资助30名贫困大学生以及奖励神木中学优秀教师。2009年底,刘还出资50万元修整了村里公路。2010年神木县“三大基金”筹款时,他捐了1000万元。随后,荣誉接踵而至。2011年,他被评为神木“十大杰出青年”,并成为当地政协委员。
政商两界的力量合拧在一起,让刘旭明头上产生了“可靠”的光环。这时的刘旭明,正越来越神秘,“言语不多,高深莫测的样子”。吴义平回忆,唯一一次让他觉得不靠谱之处是刘旭明在歌厅找了两个小姐。“那么年轻,自称一年赚30亿,却去找小姐,事业做不了太大。”
刘旭明式的成功对神木年轻人的影响非常大。当地刚毕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多数无心具体工作。他们开始向刘旭明学习,先贷款借钱,买上好车“武装”自己,出入高档娱乐场所,表现出有钱人的样子,然后再借贷盈利。憧憬富人生活的青年人,喜欢的不是单调的娱乐方式,而是当上富人的那种感觉。
山之巅峰
2011年,刘旭明的“事业”开始登上顶峰。
当年1月,他把在乌海的四个公司打包,组建了神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部设在内蒙古乌海市。公司网站资料显示,神泰集团总注册资金为1.09亿元,截至2011年4月底,集团总资产为15.2亿元,员工超过2000名,经营区域涵盖呼和浩特、包头、东胜、乌海、左旗以及陕西榆林等地。
此时,刘旭明开始向神木县的商界名流描述自己的转型愿景。谁都知道,神木500亿吨储量的煤总有挖完的一天,转型是富起来之后神木政商的主流话题。与神木之前商界名流向煤炭下游--煤化工转型不同,刘旭明玩的是高科技行业。2011年,中国多晶硅概念兴起,通过多晶硅加工获得的单晶硅,是一种既能制造高端太阳能电池,也能生产半导体硅器件的原料。
刘旭明在阿拉善盟成立了个多晶硅项目,而阿盟政府为其提供了配套条件--一处价值可期的煤矿。这样的诱惑下,神木商界名流王凤君的弟弟王凤华也加入进来,并成为吸引更多人的强力背书。
2011年11月5日,阿拉善盟行政公署与刘旭明的神泰矿业投资集团在北京举行投资协议签约仪式。阿盟盟委盟长、副书记及盟政协副主席、盟发改委主任等一干领导均到场撑台。双方签订年产3600吨单晶硅棒配套加工项目,总投资53亿元。
为此项目,刘旭明于2011年5月起从乌海回到神木,放出融资消息。由于之前积累下的“荣光”和人脉,很多政商名流争相入股,刘银娥、王凤华等都在股东行列。为了坚定大股东的信心,刘旭明亲自领着神木的十几个大老板去了阿拉善盟,晚上吃饭地点就在阿盟政府孪井滩开放区管委会,那边的领导设宴款待。“政府都参与其中,肯定不会有假。”贺峰说。
一时间,入股者趋之若鹜,李云军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看来,当时自己能入股简直就是幸运。他因远方侄子的关系,联系上刘旭明,凑了700万购买了原始股。“如果没有这个关系,700万只能放贷,入不了股。”放贷的钱月利息是3分,一年利滚利下来,1元钱可变成1.5元左右。而入股后,1块钱可变成2.8元。
这时候的神木,一片欣欣向荣,县城的房价已经涨至每平方米1万元,远超所辖属的榆林市,甚至可以和省会西安相提并论。房地产已经成了除煤炭之外,神木的另一大经济增长点。
以2010年5月的一次土地拍卖为例,当时政府拍卖了6块土地,每亩地价格近1280万元,楼面地价更是超过了每平方米6000元。高房价刺激出的新楼盘不断涌出。往北,神木新村拔地而起;往南,陕西正和房地产公司老板王和平开发的新农村项目呼家圪台的楼盘,挤到了山脚下。
7月25日,《财经天下》周刊记者来到被称为“神木第一豪宅”的麟州华府,赫然看到巨大的燃煤热力厂烟囱紧贴小区矗立,冒着白烟。就在这样污染严重的地方,一共修建了1800套住房,在土地证、预销售许可证还没有办理妥当的情形下,提前通过内部认购协议就销售一空。楼盘买主李平出示给记者的2011年7月的认购协议书显示,单价为10860元平方米。
与麟州华府一河之隔的过境路上,连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生意异常火爆。其总监杨监告诉《财经天下》周刊,之前连达以销售大众价位的车辆为主,后来根据神木客户的需求,调整了战略,专卖路虎等高档车。“最好的时候,一年卖30多辆路虎。”
当地人向记者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煤老板的儿子,买了一辆300多万元的宾利汽车,刚开出店门,就撞电线杆子上了。他赶紧下车,又去买了一辆。
庞大宏伟是榆林市销售路虎、捷豹最大的4S店之一。店里的一位李姓销售顾问表示,两年前高峰时,榆林人买200多万的路虎揽胜就像买白菜。他们都不问价格,只问有没有现车,有就马上付钱,没有现车就立马走人,去西安买去了。
根据榆林进出口部门的统计数据,整个榆林地区每年进口的汽车数量,占陕西全省70%以上。而在2012年前的几年,每年都卖出10多辆售价超过500万元的豪车。
神木县城满街的酒店,大多2008年到2011年间建成,几乎50米一家。即使如此依然供不应求,四星级宾馆更是经常爆满。稍微好一点的酒店,一个标准间的价格都在600元以上。其中几家酒店的高等级套房,都有人常年包着打牌、娱乐,即便离家一公里也不愿回。在KTV等夜店场所,一间包房一晚消费万元以上是常态。
同样的景象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也出现过。郭乐是乌海一名做土木工程的建筑商,常年在鄂尔多斯和乌海等地做生意。他告诉记者,两年多前,鄂尔多斯晚上9点后就订不到酒店了,主要消费的并非外地商旅客人,而是本地人吃完饭后去酒店开房娱乐。不少人因为怕经常订不到房间,干脆常年包着,以便随时可以去住。
郭乐的表兄赵国庆,在鄂尔多斯的一块业务是销售日本林内的燃气锅炉。在鄂尔多斯,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林内这个品牌,但只要赵国庆跟客户说“这是日本的,最贵的”,客户就买了,“鄂尔多斯人就喜欢最贵的。”
此时的神木和鄂尔多斯,以及内蒙古、山西、陕西等煤炭大省,建筑于煤炭和民间借贷基础上的繁荣场面,正显现出衰落前最后的光芒。在高利贷的刺激下,大部分资金都涌向房地产、黄金、煤矿等行业,与之无关的产业则受到严重排挤,无力发展。
全民参与的疯狂游戏,正在寻找击鼓传花的最后一个倒霉蛋。
山崩地裂
很早就有迹象表明,神木正经历盛极而衰的过程,而最该感受到这种寒意的,正是刘旭明。
2011年10月,刘旭明答应给李云军、吴义平等人的入股分红首次未能兑现。但李云军等人对刘旭明的信任并未动摇,相信接下来会再次出现利滚利的局面。就在本月,刘旭明女儿满月宴席如期在神木豪华的南亚华酒店举行,高朋满座,嘉宾云集,国内著名小品演员郭冬临、女子十二乐坊被请来表演。据称,刘旭明光礼金就收了有200多万。吴义平给的礼金是1万元,“入了2600万元的股,刘旭明就是我的上帝。”他说。
不过,厄运终究降临。为了在阿拉善盟的多晶硅项目,刘旭明修了一个办公楼,做好了基建工程。但在2012年初,项目施工开始放缓,最终停止--刘旭明的后院起火了。
如果说,2004年以来开始的煤炭价格高企,催生了神木、鄂尔多斯等地经济繁荣的话,那么自2012年起,煤炭价格的下滑,则将这些地方推向水深火热之中。
屡试不爽且高到吓人的投资回报,让神木人普遍相信两个事情:中国经济会一直高速增长下去;煤炭是中国经济必不可少的基础物资,也会一直涨下去。
可惜的是,这两件事都被证明是虚幻的。2011年底,4万亿刺激效果消失,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快速恢复的中国经济开始显露出疲态,对能源的需求也开始疲软。在煤运枢纽秦皇岛港,煤炭库存开始上升,煤价下跌了。与此同时,从尼泊尔、印度尼西亚、蒙古、澳大利亚等地进口的煤开始增多。这些地方拥有更低的开采成本,把煤挖出运到中国口岸,价格甚至比内蒙、陕西的煤还便宜。
很多煤老板认为这只是暂时的调整,但事与愿违,等了一年多时间,煤价越等越跌。仅在2013年,煤炭价格就跌了两成以上。对很多煤老板而言,煤价已经跌破了成本价,唯一的选择就是停产。有媒体甚至报道称,全神木只有7家民营煤矿还在生产。对此,神木县煤炭局的一位负责人表示否认,但他也承认,至少有半数以上煤矿停产了。
在最具“神木式传奇”的永兴乡,让村民暴富的十几家小煤矿都已经关闭。村里的小卖部生意冷清,老板本来是从东北过来挖煤的矿工,在2012年之前,每月能挣1万多块钱,但现在煤矿停产,只能开个小卖部维持生计。国有大型煤矿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柠条塔矿业公司是当地的一个大矿,该公司一位看守空煤仓的员工告诉《财经天下》周刊,他们去年裁掉了300多临时工,而正式工的工资也从之前的1万多降到了五六千块钱。这位1985年出生的年轻人对前途感到迷茫,“前年这里还挤满了来拉煤的大货车,”他指着一块空地说,“现在一辆都没有了。”
神木县政府也感受到了压力。与煤炭价格的陡峭曲线同步,2007年至2012年,神木县GDP从197亿元增长到超过千亿元。在地方举债盛行的中国,神木是极少坚持“绝不举债”的政府。其著名的全民免费医疗和教育也是受惠于此,统计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2年,神木县在各项民生项目上投入了百亿财政资金。但在几年的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之后,2012年神木已经出现了16亿元赤字。今年上半年,神木县财政总收入更是下降了三成。这样下去,神木政府“不举债”财政堪忧。
在一山之隔的山西,数据显示煤炭全行业利润同下降超过六成。山西政府开始出手救市。省长李小鹏亲自出马,与五大电力集团一家一家谈增加山西煤炭采购。一个旨在减免煤炭税费、金融支持、资源配置、现货期货交易等方面的救市“20条”也同时出炉。
鄂尔多斯比神木更先一步陷入萧条之中。原因在于,在煤炭泡沫之外,鄂尔多斯人还背负房地产泡沫的重担。赵国庆说,早年鄂尔多斯人从煤炭中赚的钱,要么借给了高利贷,要么买了康巴什的房子。而严重供过于求的房市,在2011年底煤价最开始疲软的时候,就把房地产泡沫给刺破了。去年,赵国庆收了6辆豪车,都是别人抵债的。
而神木,则越来越像第二个鄂尔多斯。在高楼林立的开发区,楼盘大多处于停工状态,而麟州华府小区的房价也从1万多跌到了7000元。“关键是,降价也卖不出去。”当地人表示,“好多外地人都走了,神木不需要那么多房子了。”
对于神木、鄂尔多斯这样以煤炭为支柱的经济体来说,当地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受到了冲击。在销售路虎、捷豹的庞大宏伟4S店,销售顾问表示,现在的销量已经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百万以上的豪车更是卖不动了。甚至之前购买了豪车的人,现在连保养车的钱都不愿意再掏,转而去街边小汽修店保养了。他们还经常接到车主的电话,让他给车估个价,准备卖掉。
酒店业的萧条则更为明显。以往一到晚上就订不到房的现象在神木已经不复存在,不少酒店都推出特价房揽客,以往要800多元的房间,现在只要200元就可以住到。不少酒店都倒闭关门,其中不乏四星级大酒店。
钱没了
突如其来的煤灾,不仅撕破了神木、鄂尔多斯的繁荣泡沫,更将以刘旭明为代表的新兴煤老板拉下了神坛。
在经济利益开始下滑的背景下,买主对煤矿购买、开采的意愿骤然下降,一些买过刘旭明煤矿的人开始找理由退矿。在乌海,刘旭明之前以1000万卖出一处煤矿。买主找到刘旭明说底下没矿,亏了本,最后刘旭明以1300万收回。对于这些纠纷,握有大把借贷资金的刘旭明似乎不在乎,用金钱继续维持着自己一方煤诸侯的形象。
但煤矿主管单位自2010年开始的煤矿整合行动,直接截断了刘旭明的财源。煤矿主管部门效仿山西省在2008一夜暴富的年的清理政策,强力推进小煤矿的整合。原本,一个煤矿年产量要达到30万吨,现在提高到60万吨。整合完成前,原来的证件由煤炭管理部门回收,煤矿停产。更关键的是,煤炭市场的不景气,让煤老板的开工意愿下降。闲下来的煤矿和空置的房地产项目,都压占了大量资金。
煤价跌了,刘旭明之前在乌海所运作的“细分煤田再出卖”模式也难以为继。断了资金来源,刘旭明后来的资金都是靠别人入股,拆后补前,寅吃卯粮。
2012年清明节,刘羽与刘旭明一起回神木万镇黄石畔村上祖坟。“那时刘旭明的情况还好着呢,没有衰落的样子。”刘羽回忆。当年7月,刘羽听到风声,很多人包括大股东找到刘旭明,要求兑现之前的承诺。刘旭明给有些人退还了本金,给有些人继续写入股收据,以利息加进去再入股。刘羽打电话给刘旭明,刘旭明表示现在退不了本金。后来,刘旭明的手机有时就打不通了,短信也不回。
在阿拉善盟项目搁浅后,刘旭明真正在意的政府配套煤矿也没了着落,要维系集资击鼓传花的游戏,他必须找一个替代品。于是,他花8000万元从阿拉善购得12平方公里“石砣山煤矿”探矿证。这给很多人造了一个烟雾弹。比如,贺峰就认为刘旭明新买的探矿权,仍然是与阿拉善盟配套的煤矿。
此时,“黄金大王”张孝昌非法集资案也在发酵之中。张孝昌宣称手中有黄金、白银矿,非法集资高达101亿,涉贷1380人,涉贷公司56家。一些非法借贷者因还不上银行贷款,被银行拉入黑名单。一时间,神木资金发条越拧越紧。
无奈之下,刘旭明只能选择铤而走险。2014年4月,刘旭明认识了神木县人大主任高崇飞之子高炎碔。刘旭明给高出示了石砣山煤矿的6个资质证件的复印件后,高炎碔入股1亿元。但随后,刘旭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李云军说,最后一次见到刘旭明是在2012年下半年,当时他带着刘旭明去西安找熟人融资,未果。2012年11月20日,一直未能看到煤矿开工也未能拿到分红的高炎碔,跑到神木县公安局报案,刘旭明的集资游戏就此引爆。被扣留之后,警方发现他的账户余额仅10万余元。
随着股东纷纷去公安局报案,刘旭明案内幕也逐渐水落石出。2012年7月至10月间,刘旭明债权人之一高峰为弄清他所称的“石砣山煤矿”虚实,曾去阿拉善盟“卧底”。他惊讶地发现,整个12平方公里只打了18个钻孔。内蒙地质矿产勘察院开始派了三台钻孔机,后来只留下一台,说是干活,其实是等着与刘旭明结账。
在此期间,刘旭明想把矿卖给一家香港公司,但因无法证明所有权而作罢。后来,刘旭明又联系北京的中植集团,再次试图出售矿产。见此情况,2012年11月,高峰回到神木后就报了案。
今年7月20日,高峰接到刘旭明专案组的电话,询问在2009年至2012年间,刘旭明名下账户是否向他的账户支付5亿元。高峰觉得此事莫名其妙,他开玩笑说:“别说是5亿,能把欠我的本金还给我就谢天谢地了。”事后,高峰想起,内蒙有一个与他同名同姓的人,而这个人正是刘旭明的放债对象。据称,这位高峰给刘旭明付过9800万的利息。
这些细节的曝光证实了一件事:刘旭明的资金流向不是买煤矿,而是在做高利贷生意,这样的风险无疑很大。
根据神木县公安局的通报,该案报案金额达7.87亿元,登记的涉案金额达11亿元。这还不是全部,因为有的入股者没报案,比如向刘旭明入股1亿元的贺峰。“刘旭明如果能出来,不用两年,一定会东山再起。”他说。
永远失去的
对于大多数中国煤老板来说,东山再起看上去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在鄂尔多斯三禾大酒店里,内蒙古昌耀投资有限公司经理石勇对《财经天下》周刊表示,自己身边的朋友,只要生意沾上煤炭的,普遍情况不妙。而他自己,也因投资煤矿被骗了钱,现在资金很紧张。石勇的哥哥甚至对记者说:“如果能拉来一些资金,我可以给你提成。”
伴随着煤炭神话的破灭和诸多煤老板的跑路、转型,以及张孝昌和刘旭明诈骗案的接连发生,此时的神木县,已经变成了频频上演狗血剧情的大舞台。
胡荣刚之前给刘旭明入股3700万元,这部分钱大都是他找朋友集资而来。刘旭明被抓后,胡荣刚去公安局报案,收回了1900万元。消息泄露后,其他几个入股的朋友要来按股权分摊这1900万,胡荣刚不愿意,打了一架后,跑路了。类似的纠纷,随着民间借贷的崩塌,在神木比比皆是。
“(合围县政府)事件的根本原因其实是经济问题。民间集资崩盘了,神木号称人人放贷,这起事件只是一个发泄的借口。”
说这番话的人叫赵兰予,3年前她硕士毕业后,回到了家乡神木县城。她跟神木很多新闻风云人物都认识。在这个小县城里,大多数人都是“熟人”。曾经轰动全国的“房姐”龚爱爱和涉嫌巨额非法集资的煤老板刘旭明,都与她相识多年。
“陕北神木人之前的淳朴、诚信,已然消失殆尽。”在当地做了30多年律师的姜雄认为,民风日下是比借贷破裂更为严重的事。
刘旭明完全改变了吴义平的生活。吴义平往日相熟的债主逼上门来,雇用东北、新疆的催债公司,在家里一住一两个月,寻死觅活。吴还曾被限制在一个宾馆里,上厕所都被跟着。
被麟州华府4套房子套牢的李平认为,现在的神木经济已退回到10年前。“那么多的楼房没人住,多少钱沉淀在里面,没有需求就成了废物。在看似平静的神木县,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血雨腥风。”他向《财经天下》周刊抱怨,自己已经52岁,老婆得了癌症,常需去西安做化疗。每天一睁眼,银行的利息和债主的眼神都让他难以直视。
过去的10年,对于他以及神木、鄂尔多斯的很多人来说,就像一场梦,梦里面坐上了过山车,看似冲到云霄,又再次俯冲下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像刘旭明一样,都回不去了。
赵兰予感叹,在这一轮大崩盘中唯一逃过一劫的,是像龚爱爱那样—把在神木赚的钱换成一线城市房产的人。当《财经天下》周刊问她有没有在西安买房的打算时,她说她想买,但现在不敢买了。“我总觉得今天中国人对房子的疯狂,和神木人当年很像。”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贺峰和赵兰予为化名)